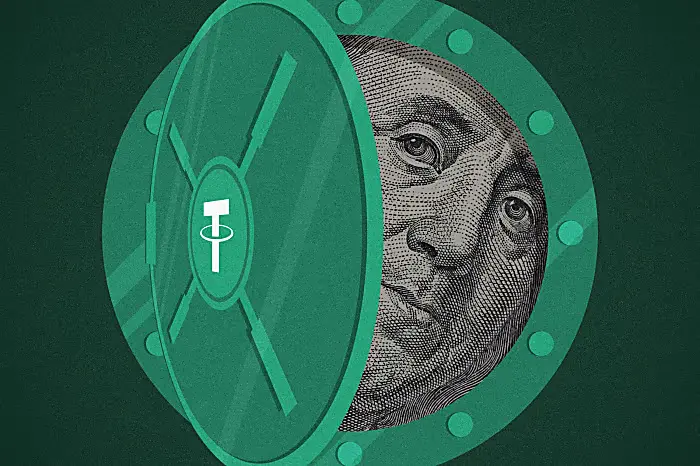對話胡翌霖:為什麼離職清華搬到新加坡,All in Web3 準備做什麼?
編輯:吳說區塊鏈
本期播客裡胡翌霖分享了他從清華大學離職並搬到新加坡的決定過程,背後既有學術體制的局限,也有對自由學術與區塊鏈生態的興趣。胡翌霖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副教授,是中文世界少有的積極參與區塊鏈世界活動的大學教師。
胡翌霖深入探討了非升即走的學術機制對青年學者的影響,分析了高校體制改革的困境。同時,他表達了對比特幣、NFT、去中心化科學等領域的深度見解,並說明了選擇新加坡作為長期發展的原因,特別是其對加密貨幣生態和家庭環境的友好性。最後,他展望了科技與藝術融合的未來,提出了如何在 AI 時代重新定義學習與教育的挑戰。
音頻轉文字使用了 GPT,可能會有錯誤。收聽完整播客:
離開清華的原因
Colin:各位聽眾,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我們播客的老朋友胡老師的身份是清華大學科學史系的副教授,但是現在胡老師已經離職,搬到新加坡了。胡老師,要不您自己講講,這個過程是怎麼回事?
胡翌霖:算是 ALL IN Web3。首先糾正一下,也不算辭職,算是自然的離職。現在的年輕學者其實挺卷的,都是要經歷非升即走機制。非升即走就是說你必須在 6 年內通過長聘評審,如果沒通過就得走人。我決定不參加評審了。
"非升即走"這個機制是清華帶頭搞的。清華和北大率先實行了這個制度。它是學美國的學術體系,但說實話,美國的學術界也不怎麼樣。再加上,中國借鑒的時候也有一些變味了。不過,說實話,清華相比國內很多高校還是好很多的。我在清華的感受是,至少清華相對尊重老師。
雖然我離開了清華,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滿。主要是清華還是比較尊重老師的。這裡的尊重分兩個方面。一個是把老師當"自己人"。很多高校實行非升即走的機制時,會把老師當成臨時工,趁著青年學者在 35 歲以前的黃金期壓榨他們的研究產量。清華相對還好一點,它更注重論文的質量而不是數量。清華採用的是代表作機制,論文只需要達到國際或國內領先水平就可以,不要求數量特別多。所以這點我覺得還是可以的。但即便如此,我最終還是選擇離開了。今年正好是我合同期滿的時間,順其自然就離開了。
其實我是跟著吳國盛老師從北大來到清華的。我屬於清華科學史系的元老之一。我們科學史系當時一批元老,現在都走了。很奇怪的是,科學史系沒有一個年輕老師通過長聘。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各有各的原因,但最後都沒留下來。
有人去了國外,有人去了其他學校。也有人沒通過評審,沒轉正,還有的選擇轉行,比如去修道的。總之,各種情況都有,各走各的路。
學術體制改革的困境
Colin:看來現在高校和以前真的不一樣了。以前感覺進了高校就像進入體制內,慢慢混日子就行了,現在似乎壓力變大了。
胡翌霖:對,這就是學術問題的核心。我們可以順便聊聊去中心化科學(DeSci),也就是關於學術和科研的去中心化問題。我對此很有感觸。無論是傳統學術模式還是當下的學術模式,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存在很大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已經不太適應現在的發展。
以前清華北大帶頭改革,其實某種意義上是必要的。傳統模式下,學術界很多時候變成了"佔坑遊戲"。比如,一個教授佔著一個崗位,研究好壞都沒人管,特別是在文科領域。有人佔著一個坑,無論研究是否出色,這個職位就是他的。這種模式確實不利於學術流動,也很難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於是後來改革出現了"非升即走"的機制,把鐵飯碗變成了臨時工。
所謂非升即走,一般是一個六年的機制。你博士畢業後的前六年是學術生涯的黃金時期,但在非升即走機制下,這段時間你是臨時工。為了通過評審,你需要拼命發論文,拼科研課題,卷到極致。成果全歸學校,但你可能還是評不上長聘,只能走人。
之後呢?你可能去二流、三流院校,甚至找不到工作。而此時你已經過了學術產出的黃金期,研究產量下降,工作機會也更少。這種模式對於學者來說並不友好。
不過,在相對平衡的環境下,這種模式也許還可以,比如清華。清華的非升即走機制給了一定壓力,但沒有那麼苛刻。研究相對自由,教學也受到重視,卷的程度較低。不過,這種環境很少見。清華的致命問題是經費不足,薪資待遇低。這就像在職場裡,薪資高的地方比如大廠會卷生卷死,而清華這種錢少的地方壓力可能稍小,但也存在矛盾。
從更大的趨勢來看,這種"卷"是無解的。我曾看到一篇文章把大學教職比作"龐氏騙局"。尤其是人文學科,博士的最佳出路就是去高校任教,但教師崗位是有限的。一個教授可能培養 20 個學生,這些學生再培養更多學生,形成無限擴張的需求。然而,實際的教師崗位並不會增加這麼多。
過去,中國和西方的大學擴張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個問題。比如,人口增加、教育普及帶來了更多高校需求。但當擴張結束,比如現在人口萎縮、教育需求趨於飽和,問題就暴露出來了。未來大學將進入萎縮期,這種機制會越來越不可持續。
Colin:沒想到學術界也是一個龐氏騙局,和幣圈很像啊。
胡翌霖:是啊。很多學科都有類似問題。像我所在的科學史學科適應性稍好一些,因為我們承擔通識教育任務。但一些較冷門的專門學科問題就很嚴重。一個教授培養的學生往往只為接班,如果每代只招一個學生,課程都開不起來。而開課就需要更多學生,可這些學生將來幹什麼呢?這就是模式不可持續的原因,必須改革。
中國和西方都有這個問題,但中國的問題更嚴重。中國用了十幾到二十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一百多年的擴張節奏。這種快速擴張使得中國學術界更難適應急速萎縮的環境。西方也有類似問題,但節奏稍緩,相對更有時間調整。
離職後選擇新加坡的原因
Colin:胡老師,那您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考慮離開高校的?又為什麼選擇新加坡呢?這和 Web3 或者區塊鏈有關係嗎?
胡翌霖:離開高校的想法其實一開始就考慮過。因為我本來就沒把高校當作"鐵飯碗",所以一直會想,如果沒通過長聘怎麼辦。當然,如果沒通過清華的長聘,我還是可以去國內的一些一流高校,不能叫二流,畢竟清華是超一流,去一般的一流大學找教職應該問題不大。但問題是,要不要繼續在高校,或者乾脆不幹了,轉向自由學者,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我之所以教書,並不是為了找個"飯碗"。作為比特幣玩家,我們的觀念是不相信所謂"鐵飯碗"的。這種東西看似穩定,但實際上並不可靠。即便是終身教職,也不是真正的鐵飯碗。如果整個系統崩潰,龐氏騙局維持不下去,所謂的鐵飯碗也就沒有意義了。另外,就算有鐵飯碗,飯也可能越來越少。
以清華為例,它的工資待遇非常低,是出了名的。清華在體制改革早期靠高薪吸引人,但不給終身教職,提供的高收入和好待遇在當時還是非常具有競爭力的。然而,現在全國其他高校也開始搞準聘機制,但他們的待遇提升了,而清華的待遇卻基本沒有明顯變化。這樣一來,雖然清華的"飯碗"還在,但飯已經不夠吃了。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鐵飯碗"反而成了"鐵束縛",阻礙你跳到更自由的環境中去發展。
儘管如此,我在清華的日子還是不错的。因為我不靠工資養活自己,而是享受教學帶來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是錢買不到的。你用心準備的課程和理論,能夠影響那些優秀的學生,這種感受是不可替代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成就感也在變化。例如,培養博士生的時候,你會為他們的未來感到負責,但你知道,他們最終會進入學術界的龐氏騙局。這種矛盾讓我的教學成就感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我這些年和幣圈很多人交流,也感受到了一種成就感。我發現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能夠影響更多人,並收到積極的反饋。這讓我意識到,傳播思想並不一定局限於高校。走出高校,可能會面對更廣闊和更有效的信息傳播空間。這也是我最終選擇離開的原因之一。
Colin:那您為什麼選擇新加坡呢?這個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嗎?
胡翌霖:其實沒有考慮很久。我第一次來新加坡就定下了,一開始其實是考慮去香港的。
香港是第一個選項,因為比較方便。作為一個比較宅的人,我不太願意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比如和外國人打交道,對語言和社交都不太擅長。我希望能在華人多的地方,同時又有一定開放性的環境。香港看似很適合,但後來發現幾個問題。首先,很多人都說"潤香港不如不潤",意思是去香港並不算真正的移居。其次,香港的生活環境讓我感到壓抑,尤其是對孩子來說。如果一個小孩長期生活在狹小的空間,心理健康可能會受影響。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生活環境寬敞舒適很多。
另外,新加坡的人很親切。雖然我在香港的短期經歷還不錯,但總體感覺香港人有點"死氣沉沉",比如有些服務員給人的感覺像是我欠了他們錢一樣。而新加坡的人則更熱情友好。再加上,新加坡的移居手續相對簡單,比如申請 EP(就業准證)不算太難。雖然永居難度大,但作為一個居住地並不困難。
總結來說,我選擇新加坡的原因有三點:
第一,華人友好;
第二,對加密貨幣生態相對友好;
第三,對富人友好。社會秩序穩定,雖然這對社會活力可能不是好事,但對不需要打拼、已經處於富裕階層的人來說非常友好。
科技史與區塊鏈研究的結合
Colin:胡老師,您目前的生活安頓得如何?未來有什麼計劃嗎?是會繼續從事學術相關的事情,還是更偏向 Web3 和區塊鏈相關的工作?
胡翌霖:都有吧。首先,我最大的任務是安頓好孩子,這是首要的。其次,在這個前提下追求自由,我現在已經把學術和 Web3 融合在了一起。這種融合從一開始就是一致的。我之前也提到過,比特幣圈子其實是我博士論文的直接產物。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我思考了貨幣的本質,以及為什麼比特幣是正確且有價值的,想通之後就進入了這個領域。可以說,從一開始到現在,這就是一個知行合一的過程。
我的學術方向是科技史,尤其偏向技術史和技術哲學。技術史很有趣,因為它展現了人類歷史上真正推動變革的力量。相比政治史和王朝更迭等,技術史帶來的變革更加深刻和劇烈。政治史中常常是換湯不換藥的循環,但技術史則是持續的進步。比如,文藝復興、科學革命以及工業革命,這些都得益於科學和技術的推動。從透視法、印刷術,到航海技術,再到現代科學和工業體系,這些技術革新對人類歷史的推動是非常波瀾壯闊的。
技術史讓我們看到這種壯麗的變革,甚至可以讓我們親身參與其中。這是它令人著迷的地方。而科幻則從另一個方向看待未來的技術變革,描繪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面貌。技術史探索過去,科幻暢想未來,但現在巨變真正發生在我們現在所處的時空中,我們感覺自己不斷遭遇歷史性的時刻,不斷見證科幻成真,這種感覺是非常震撼的。
這種結合讓我有一種使命感,就像參與人類命運詩篇的新篇章一樣。這種體驗感是激動人心的,也是一種知行合一的體現。研究歷史的意義不僅僅是對過去的記述,更是對當下行動和判斷的啟發。歷史不會直接告訴你該做什麼,但會通過情感和經驗的渲染給你啟發。
比如,看一部小說或連續劇,如果看了前面的部分,再看新的一集時,你會更有參與感。因為你會將當前的情節放入一個宏大的敘事中,理解得更深入。對我而言,把當下的事情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中看待,會增加我的投入感。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並不僅僅是為了賺錢養家,也不是為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是為了參與一場更偉大的人類浪潮。雖然這種浪潮的意義難以確切定義,但它帶來的體驗感是非常強烈的。
比特幣投資、持倉策略及冷錢包
Colin:胡老師,咱們聊點幣圈實際的事情。大家比較關心的是您的持倉比例,絕大部分還是比特幣嗎?您是從早期就持續加倉,還是主要靠早期買的比特幣為主?
胡翌霖:嗯,這個問題其實也不是特別複雜。我從入圈的時候就開始記錄,我記得自己當時說過"攜幾千資金殺入幣圈",這些內容在我的博客裡都能找到。雖然我入圈時間很早,是 2013 年,但我現在也沒太多錢。很多人會覺得奇怪,我 13 年入圈,一直是 HODLER,也一直倡導持幣,但為什麼沒賺到特別多?原因很簡單,我當時是個窮學生,沒有收入,能投入的資金很少。
我最早是從生活費裡一點一點扣錢來買比特幣,後來還被我爸批評,說生活費是用來生活的,不是用來投資的。後來拿了獎學金,就用獎學金買了一些。所以最初的資金也就幾千塊。這是我的原始資本,之後我一直在加倉。今年我還在加倉,因為我搬出國後,把國內的一套房子賣了,用這筆錢繼續買比特幣。
Colin:現在價格這麼高了,您還在加倉?
胡翌霖:是的,我還準備繼續加倉。長期來看,我相信比特幣總能跑贏法幣。
Colin:之前聽到神魚提過一個"四錢包理論",大概是 60% 的主流資產,比如比特幣,放在冷錢包裡;20% 做一些靈活操作;10% 做高風險投資;5%~10% 留作法幣。您的策略和這個理論類似嗎?
胡翌霖:我不太認同他的理論,尤其是關於法幣的部分。他提到用法幣利息覆蓋生活成本,這個比例對普通人來說幾乎不可能實現。只有像神魚這種大佬才能計算出這種尺度。普通人根本無法做到。
我的策略是基於比特幣本位。我把所有資產的 4% 用作生活成本,而這些資產不需要轉換成法幣去吃利息。我的生活成本直接用比特幣的年增長率覆蓋,因為比特幣的增長率遠遠高於傳統法幣的無風險利率。
Colin:那您會把比特幣拿去質押升息嗎?還是放在冷錢包裡?
胡翌霖:質押升息的話,我只會拿出少量資金玩一玩,比如半個幣或一個幣。對我來說,這只是嘗試,並不會把大部分資產投入進去。我之前嘗試過不少,比如梅林和藍盒子,最後來說虧了不少。當然這些嘗試更多是為了體驗前沿玩法。
Colin:有時候忍不住看到項目做得好,還是會買一點吧?
胡翌霖:確實如此,尤其是在 NFT 那波行情中,我當時沒忍住,買了一些,結果虧了不少。雖然最近 NFT 市場又熱了起來,但我的資產只是從"腳脖子"回到了"膝蓋"而已。
Colin:那您對冷錢包有什麼建議?您用的是什麼錢包?
胡翌霖:我的主要資產放在比太錢包。比太錢包挺早的,團隊很早就解散了,但這個錢包不用升級,現在仍然很好用。我覺得它是冷錢包中最好的方案之一。它的模式是使用一部舊手機作為冷錢包。我們幾乎每個人都有閒置的舊手機吧?
你只需要在舊手機上安裝比太錢包,然後斷網,刪除藍牙和 Wi-Fi 功能,這樣這部手機就變成了冷錢包。再在另一部新手機上安裝熱錢包,通過二維碼簽名進行操作。這種方式既簡單又安全,而且成本很低,不需要額外購買硬件錢包。
Colin:比太錢包和比特派是一家公司吧?
胡翌霖:是的,但後來比特派推出了硬件錢包,比太錢包這種模式因為不賺錢被放棄了。我可以理解,畢竟這是一個開源軟件,又沒有盈利點。但我很喜歡這種模式。
另外,我建議大家把助記詞背下來。我自己背了幾套助記詞,這樣即便是冷錢包出現問題,資產也能很安全地恢復。
比特幣生態與 ETH 生態的對比
Colin:胡老師,您之前在比特幣生態上做過一些 NFT 項目,但最近似乎整個行業的熱點從比特幣生態轉移到了 meme 幣上。您覺得比特幣生態未來還有機會嗎?還是說您也會關注其他生態,比如 Solana 或者 Base 上的熱點?
胡翌霖:我並不排斥 meme 幣,這些項目是可以玩的。說回比特幣生態,我其實一直看好它。但比特幣生態目前的問題是,它還沒有找到特別好的發展模式,也沒有建立起足夠強的認同感。
從整個行業來看,比特幣生態有它的獨特性,而我當初看好它的一個原因是,它能成為對抗 ETH 生態的一種選擇。ETH 生態的問題在於定位模糊:它既想堅持去中心化、秉承朋克精神,但在許多方面又走向了中心化。而它在去中心化上比不過比特幣,在效率和節奏上又比不過 Solana。
Solana 的定位很明確,它就是中心化,效率高、節奏快。這種定位吸引了那些注重用戶體驗的人。如果你想要更高效的鏈,那就選 Solana。相比之下,ETH 有些不上不下,兩頭不討好。
而 Base 作為一條公司鏈,也更傾向於中心化方向的發展,目標是提升效率。儘管不能說它完全是中心化的,但它比 ETH 更加中心化,走了一條明確的效率優先的道路。
我看好比特幣生態的原因是它代表了去中心化的理想。作為去中心化的信徒,我認為這一方向仍然是正確的。但比特幣生態目前的困境在於兩頭不討好。一方面,比特幣的 HODLER 們並不認可生態中很多新項目,認為它們本質上還是在"炒幣",是山寨幣的變種。另一方面,對於喜歡炒幣的用戶來說,比特幣生態又效率低、節奏慢、流量小,吸引力遠不如 Solana 生態。
作為比特幣 HODLER,我們本身是很保守的。能夠拿出 1%、2% 的資產來參與這些項目已經不容易了,但要讓我們 ALL IN 或者重倉押注,這是不可能的。正因為這種保守,比特幣生態很難吸引到傳統的比特幣玩家,同時也沒法爭奪到喜歡短期收益的投機用戶。
儘管如此,我認為比特幣生態仍然有機會。比如,未來可以不再追求"炒幣"的節奏,而是做一些長期價值的項目。比特幣上的 NFT 可能就是一種方向。因為比特幣具有更強的"永恆性"和"堅固性",在 NFT 領域可能更具說服力。
未來比特幣生態的突破可能依賴下一代 NFT 產品。這些產品需要跳脫單純炒作的邏輯,擁有更多實際的玩法或價值。如果這些新模式能夠與比特幣生態適配,我相信它還有機會重新崛起。
去中心化科學的可能性與問題
Colin:胡老師,您接下來有哪些探索計劃呢?是繼續圍繞藝術相關領域,還是像之前我們聊到的,去中心化科學(DeSci)這方面會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胡翌霖:關於去中心化科學,我必須承認,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非常想做這件事,但目前我沒有足夠的行動力,也沒有精力去真正推動這件事情。這個領域任重而道遠,非常難。所以,如果有人願意做,我會全力支持,比如做參謀、顧問,甚至站台。我一般不會輕易為項目站台,但如果這個項目是真正朝著去中心化科研方向發展,並且符合我的理念和標準,我是願意支持的。
Colin:確實,有些項目一開始就以發幣為目的,看起來更像是圈錢騙局。
胡翌霖:對,確實有些項目太急功近利了。比如一開始就急著發幣,這樣反而透支了項目的潛力。實際上,去中心化科研的核心問題並不是資金,而是影響力和共識。如何建立起學術界的共識,這是關鍵。
僅靠資金是無法推動科研發展的。如果砸錢能解決問題,中國早就有一大堆諾貝爾獎得主了。中國並不缺資金,問題在於科研需要時間、氛圍和文化的積累。這種積累是砸錢砸不出來的。比如北大,雖然資金並不多,但無論是理科還是文科,它的底蘊非常深厚。這種底蘊並不是靠砸錢就能立刻複製的,清華或其他學校也無法短期內達到這種高度。
去中心化科學和去中心化金融的道理是一樣的。很多項目一開始就發幣,說白了就是為了融資圈錢,但去中心化科學並不缺錢。科研發展的真正矛盾在於它需要時間去建立共識和文化氛圍,而不是一上來靠發幣吸引短期利益。
不過,我並不是完全排斥發幣。早晚發幣是可以的,但它不應該是一個項目的起點,而應該是後期發展的工具。去中心化科學需要的是更長遠的規劃和更扎實的推進,而不是一開始就透支預期。這樣才有可能真正推動這個領域的發展。
未來規劃:科技與藝術的融合
Colin:胡老師,您可以考慮找幾個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個專門的播客。比如說針對您感興趣的去中心化科學領域,每週做一期節目,我覺得會很不錯。
胡翌霖:謝謝建議!其實我確實有類似的計劃。我之前在香港租了一個工作室,原本打算用來探索數字藝術。將來也可能會開展一些節目形式的內容,不一定是播客,可能是視頻節目或者其他類型的創作。我們那邊有一些比較先進的 MR 系統、XR 系統,還有一些與數字藝術相關的場景設計。所以,我們可能會在視頻號、YouTube 或者哔哩哔哩上發布節目。這個節目可能既包括藝術,也包括科技,甚至涵蓋學術和去中心化科學等主題。
我們對科技與藝術的結合有一些深入的思考。技術與藝術的分裂實際上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是工業革命之後才逐漸出現的。在更早的歷史中,技術和藝術是合而為一的,甚至連詞彙都沒有區分。比如"art"這個詞,既可以指技術,也可以指藝術,還可以指知識。這種分裂是 18 世紀、19 世紀甚至 20 世紀的產物。我們認為,這種分裂可能在未來進入一個新的融合階段。正所謂"分久必合",未來技術與藝術有可能再次走向統一。
這種新的融合不僅僅是藝術與科技的結合,還涉及哲學、科學,甚至學術的整體走向。比如我們前面討論的大學的功能問題:大學究竟在培養什麼?目前的教育模式是否只是在不斷製造"接班人"去佔學術資源的坑?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僅人文學科存在龐氏騙局,理工科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許多專業培養的人才,現在看來是可以被 AI 替代的。大學長期以來把人力資源作為主要的培養目標,但在 AI 時代,這些人力資源已經逐漸沒有優勢。AI 的更新速度遠遠快於人類的學習速度,人類一代人的周期可能需要幾十年,但 AI 幾乎每天都在進化。
因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學習的意義。從廣義上說,人類為什麼要學習?應該學習什麼?從狹義上說,大學的未來是什麼?雖然許多大學可能會在轉型中消失,但一些人類文明的重要傳承仍然需要被保留下來。那么,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學習和教育,這將是一個很大的課題。